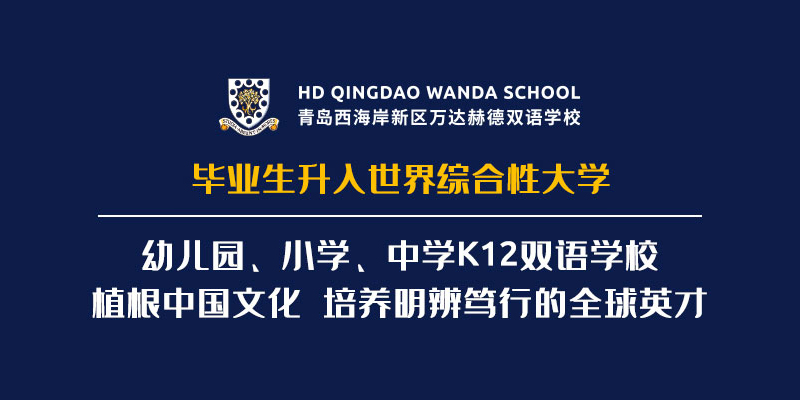高峰对话丨是先成功才幸福,还是幸福的人才能成功?
AI的快速迭代正在重塑世界,也在重构未来的学习。当信息洪流让世界变得“触手可及”,青少年为何反而遭遇“空心病”的侵袭,找不到幸福感与意义感?当未来充满变化,“不确定性”成为常态,家长开始不断寻找“成功路径”,忙着为孩子成长规划最优解。AI时代,如何真正让每个生命蓬勃生长?教育的本真究竟去往何方?
面对这样的教育迷思,教育者们从未停止探索。清华大学教授彭凯平从积极心理学出发,为教育锚定了“情绪与意义共生”的核心;义格教育集团董事长、赫德赫贤学校创始人孙涛从自身经历出发,在校园里探寻“我是谁”“何谓幸福”的人生命题;产品战略专家梁宁则以“真需求”为切口,追问如何守护孩子的精神成长。
近日,义格教育集团举办的“首届儿童青少年积极教育大会”上,三位嘉宾齐聚圆桌,围绕“积极教育如何赋能学生终身幸福与全面发展”的核心议题,从家庭关系到校园建设,从情绪价值到生命力唤醒,展开了深入对谈,为迷茫中的教育者与家长,点亮了回归生命本真的教育方向。
今天的孩子,为什么不开心?
冯澍:非常感谢各位参加首届儿童青少年积极教育大会!我们都说积极教育其实是幸福的科学和幸福的教育。首先请问三位用最简短的话表达一下,你们的心目中幸福是什么?
梁宁:对我来讲,幸福就是我和我关注的人或事的关系,大家可以安然共处,这就是幸福。
彭凯平:积极心理学对幸福有一套科学定义,就是PERMA模型。幸福要有情绪、有沉浸、有关系、有收获、有意义。我把它简化为两个:一是快乐,就是愉悦的情绪;二是赋予这个快乐以积极的意义。
简单讲,幸福就是有意义的快乐。
孙涛:刚刚坐在会场里,我就感受到了幸福。我知道自己在这里,感觉跟周遭的一切,好像跟每个人的呼吸都是共通的,那种无我的福流状态,让我特别幸福。
冯澍:此前听硅谷投资人纳瓦尔谈幸福,他的答案是“接纳当下的我,这就是幸福”。回到当下,我们的物质生活已经极大富足,孩子的物质需求也得到了很大的满足。但我们也看到,越来越多的孩子不快乐,从“空心病”到“四无孩子”,这个问题变得愈发严峻。
现在的孩子,为什么不幸福?这引发了我们对教育怎样的思考?面对教育选择,当越来越多的家长希望“既要又要还要”的时候,到底什么才是当下教育的“真需求”?
梁宁:过去两三年,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。之前我们学习是为了得到知识,送孩子去上学,好像要让他变成“知识容器”;再用一系列考试来判断这个容器的“容量”。但是今天,最好的知识容器就是AI。我们给AI灌知识就好了,为什么要灌一个孩子呢?
我们的教育制度、社会协同制度,都是工业时代过来的。过去我们常说“学以致用”,也就是在一个特定环境里,用封闭的知识,完成制定的任务。这项工作做得最好的,不就是AI和机器人吗?
所以今天,也许教育的目标要变了,变成“学以成人”。我们不是把孩子做成知识容器,而是让孩子在学校的框架里,成为一个更完善的人。在获取知识的同时,他要有精神的成长。
其实每个小孩子,都有非常蓬勃的精神,他有无尽的好奇心、探索欲,会一直问问题。但随着孩子长大、升学,他的好奇心在下降,有越来越多的东西不想探索。我们会发现,随着年龄增长,很多人的精神反而在坍塌。所以我一直在想,教育是不是可以有更多选择,精神要如何成长?
冯澍:这个问题我想抛给孙涛先生。赫德、赫贤学校已经走过十多个年头。您作为学校的创办者,三个孩子的父亲,如何看待教育这几年的变化?您又为什么要把积极教育作为赫德、赫贤学校未来一个重要的战略方向?
孙涛:11年的办学之旅,现在回头看,更像是我的一场自我探索,包括“我是谁?”“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?”
今天我们很大的焦虑都来自“不确定性”。随着AI大潮来临,随着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变化,大家都在焦虑。我的孩子到哪里读书?学什么专业?将来从事什么工作——大家都在试图寻找那个确定性的答案。
我考大学那时候,是先填志愿后考试。那时没有互联网、宣讲会,我就看到了北大的宣传海报,觉得北大好漂亮。我说,我想去北大。我妈说:“你疯了?北大理科全省只招6个人,你连年级前30都没进过。”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,我说今年考不上,明年肯定能考上。我很幸运,考上了。
回头想想,过去没有那么多信息,没有那么多确定“路径”,反倒让选择简单了许多。但今天,社会上好像有某种“任务清单”,好像你只要完成这些任务,达到怎么样的条件,你就会找到一份工作,你做了什么样准备,就能进某个行业,在多少岁时能赚多少钱,然后你就幸福了。
但这恰恰是我在创办赫德、赫贤学校之前,最大的不幸福感。我貌似过上了那种别人眼中“幸福的人生”,但我并没有感觉到幸福,我没有找到生命的意义。虽然关于“我是谁”这个问题看上去很大,但我觉得,应该是在孩子们走进青春期后,需要帮他们一起去思考的。
过去的11年里,我看到了所谓“确定性”的进一步坍塌。过去,哪怕是海外升学,也好像有某种公式,家长们也会功利地选择学哪个运动、选什么乐器、参加什么社团更容易进藤校,但很少有人真正去思考,这些是孩子的真需求吗?
或者,我们作为家长的真需求是什么?答案是肯定的,我们希望孩子幸福。但人不是因为成功才幸福的,大概率是因为你幸福了,进入福流(flow)的状态了,你才会成功。就像梁宁老师在《真需求》里写道的,优秀的组织都是因为做自己,真实地做自己,才变得成功。所以成功跟幸福并不矛盾,但我们把方向搞反了。
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开启这样一场对话,开启未来下一个10年的教育,我希望跟大家一起思考,什么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,那个“我”是谁?我们来到世界的意义是什么?随着不确定性的进一步加剧,家长也在怀疑所谓的成功路径,我们也就有机会去实践这样的教育。
如何建构学校与家庭的积极教育生态?
冯澍:下一个问题想请问彭凯平老师。我们都知道积极教育的可贵,但目前整个教育的大环境仍然充斥着内卷,评价体系也相对单一。如果我们想在家庭、学校中构建一个积极教育的“微生态”,需要怎么做呢?
彭凯平:我们最近开始在学校进行积极教育实践。我觉得在学校层面,有五个努力的方向。
第一条就是还是要有一支队伍,学校应该有一个“心理副校长”,主要管这方面的事情。另外我们要有一支对心理学有经验、有热情,愿意帮助学生、老师的心理学工作者队伍。
第二就是要有一套课程,这个课程就是我们讲的生命教育,积极教育。而且我希望这个课程是一个公开、显性的课程,而且要把它变成全校都可以学习的通识课程,或者叫做学校的基础课。
第三要有一个空间和平台。人受环境影响特别大,所以一定要有一个空间,大家可以来谈心、说话、交流、沟通。这个地方要有一些清香的气息,要有温暖的环境,让人可以放松下来。
第四要有一套仪式,把幸福做成行动。这个行动就是每天问候别人,就是要给孩子微笑的时间、行动的时间、户外活动的时间、做游戏的时间……把积极的能量通过行动化解出来,并把它变成一套系统,融入孩子们的生活习惯,形成有一套仪式,因为人其实是一种仪式的生物。
最后就是要有一种文化,最重要的就是评价体系。我们以前的评价体系都是学科成绩,让大家很内卷。我们可以创造一种全新的评价体系,看看有多少孩子阳光灿烂,笑得比较多,跳舞跳得好,打球打得不错,做善事做得比较积极。我们找到这个评价体系,整个文化就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家庭层面的积极教育怎么办?我当年提出过一个“3C原则”。
第一个C叫作Companion,陪伴。我们回家的时候一定要有陪伴的时间,换句话说就是一定要有家人在一起的时间。
比如说家庭会议。其实大家不要以为家庭会议,现在家庭会议有个毛病,就是那个妈妈在那指导大家,训大家。我觉得家庭会议就是大家闲聊,今天上了什么课,做了什么事儿,遇到什么人,聊一些轻松的、愉悦的、启发智慧的事情。如果这种会议听起来比较正式,那我们就利用吃饭的时间闲聊。甚至孩子做作业的时候我们去陪伴,但不是监督,而是可以在旁边看一些愉悦的书。
第二个就是Communication,沟通。
70年代有两个人类学家做了一个很有趣的研究。他发现中产阶级的孩子上大学、出人才的比例,都要比底层的孩子要高。原因是什么?他就发现中产阶级的父母亲跟孩子说话多,平均三年下来,如果能够说达到3000万单词,这个孩子的未来的智商要比同龄人高10分到30分。所以家长要多哄孩子说话。跟他聊聊一些没有答案的问题,不要聊政治,而是多聊一些为人处世、人情世故的话题,这个叫作Communication。
当然除了说话之外,还有拥抱、非言语沟通,一个爱的欣赏,一个温情的拍拍肩膀,打打闹闹,嘻嘻哈哈、勾肩搭背,一定要把咱们中国那种父道尊严的封建式的想扔到太平洋里去。
最后就是要有Culture,也就是家庭的文化氛围,家里可以有些制度,比如一定彼此要关怀,父母不要把工作烦恼带到家里来,不要当着孩子批评丈夫或者妻子,要维护彼此的尊严。这是特别重要的技巧。
冯澍:彭老师的这几个观点,让我联想到了梁宁老师在《真需求》中讨论的“情绪价值”。在这个时代,情绪价值正在变得非常重要。梁老师,在您看来,情绪价值在教育中有怎样的体现?
后来我发现,接纳自己非常重要,我们要知道自己生来具备的品质。孩子都是“本自具足”的,比如在赫德、赫贤幼儿园,每个孩子都是超级自信、非常自在的。他们可以唱歌跳舞,相信自己就是超人,也不会有所谓的羞耻感。
但为什么长大就慢慢变了?他们越来越自我怀疑,越来越跟随周遭的定义。周围的人也许都在说:你还不够好,你要变得更好。 我们都希望看到一个孩子最本真的样子,心中有爱,眼里有光。但我觉得最重要的,应该是首先要让孩子知道,你是可以的,你什么都有,你就是那束光本身。
我们要在学校构建一个安全、温暖、有爱的环境,给孩子更多体验的机会,包括学术的、体育的、艺术的,各方面体验。让他能在各种体验中去发现自己的优势,从而更好地接纳自己。
积极心理学也并不是主张你一定乐观,而更重要的,是培养一种心理韧性,在你悲观沮丧的时候,你会知道“这也是可以的”。积极心理学也不是要求你一定做到什么,而是真正的自我接纳。有些天赋你注定没有,但你可以找到自己的与众不同之处,接纳自己,建立自信,探索更多可能。
在学校里,如果我们能构建安全的环境,让孩子可以犯错,可以表达情绪,允许一切可能,允许孩子按自己的生命节奏去成长,孩子才能更好地成为他自己。我很喜欢这次积极教育大会的主题:Empower every child to flourish,让每个生命蓬勃绽放。Empower的意思是赋能,孩子本来就有,我们只是帮助他们看到自己,看到那个无所不能的自己。这就是我们作为教育者和家长,能做的最好的事情。
四、AI时代,最宝贵的是“生命力”
冯澍:教育就是被允许、被看见,让每个生命蓬勃绽放。在AI时代,我们经常看到各种讨论,有哪些我们人类的特质是不能被AI取代的。那么,我想最重要的,应该是我们生而为人的生命力,我们都是有生命的、活泼泼的个体。想请问各位,是如何定义“生命力”的?以及,你们对未来教育有怎样的憧憬?
梁宁:薛定谔说,生命以负熵为食。我们建构秩序,输出秩序,这就是我们生命的痕迹。
如果把人和AI对比,人类最大的特点就是“在乎”。AI有算法,知道正确答案,但人有发自内心的在乎,它让我们对真相的追求不停留在表面,对答案的要求不停留在标签,而是一直向前探求。如果一个孩子知道了自己在乎什么,他就有了一路向前的线索。